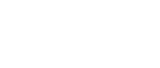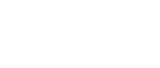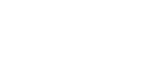心有千结是乡愁 (杜中伟)
| 招商动态 |2016-12-22
今年十月一长假期间,回到赵县老家探访了几处古迹——尚谈不上是名胜,因为既没有名胜的声名,也没有名胜的模样。大多数都沉默于郊野,泯然于荒丘。于是回来写了几篇文字,题目统一为《寂寞赵州》。写写赵州,写写家乡,一直是萦绕在心头而挥之不去的情愫。虽然,有时候也对家乡的种种有些失望,甚至有些愤怒,但内心深处还是对家乡,对这个历史军事重镇、文化名城有着刻骨的热爱。这便是植根于内心的家乡情怀。
我写过《赵州赋》,又写了《寂寞赵州》,还写过《大地无言》、《太阳的颜色》,都是基于对老家、对父老乡亲的热爱、敬重,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大地无言》、《太阳的颜色》写于小20年以前了,当时大学毕业时间不长,回家也多,看到这里的大地,看到这里的人们,总会产生一些感悟,于是就把这些感情写了出来,这里面是浓重的情感。
只因为自己生于斯,长于斯。
始终忘不了这一片广袤而生机勃勃的田野。这是上天赐予中国最好的一片土地:四季分明,土壤肥沃,交通便利,一望无际。在农耕文明久远的中国,土地是根本,这也是上帝对这一方百姓的眷顾。纵然在历史上从不缺乏苛政猛于虎的时段,但这方土地的收成总还是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能够苟活并且绵延下来。而随着时代的前进,这片土地养活了更多的人,上达庙堂,中至江湖,下见布衣。
当下正值隆冬。窗外是灰茫茫的一片——正赶上近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雾霾天气,各种吐槽,各种段子,也只是无奈、愤怒和叹息。这种无奈、愤怒、叹息不仅仅是对天气,还有其他。
我便更加留恋曾经经过的那片土地。
正是在冬季。
旷野尤其显得空旷而博大,过冬的小麦覆盖着或厚或薄的雪,也可能仅仅是一层霜花。已经天寒地冻。西伯利亚寒流从北而来,在这里撒着欢儿地肆虐,吹得树梢、电线“呜呜”作响,卷得尘土和草木的枝叶漫天飞舞。父老乡亲们已经忙完一年的农活,便闲散起来。那时候打工的氛围还不是很浓,我们的父辈们再也不像在他们年轻时要战天斗地地去穷忙活。忙活了一年的他们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高高兴兴地准备过个好年。如果是要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盖房的话,就要在入冬前打上几架坯。这是在过秋之后唯一的强体力的劳动了。而我们还要顶着风骑着自行车上学去,有时候由于风太大,只好下来推着车子走,竟然没感觉到辛苦。那时候,并不知道雪莱,也不知道他的《西风颂》,但知道春天是早晚要来的。而在心中,却没有想这些,大概就是想的千万别迟到,甚或什么也没想。
而春天却不会迟到。
春天当仁不让地是一年中最美的一个季节,这里的田野也当仁不让地成为四季当中最美的。一碧万顷,是毫不夸张的。绿油油的麦子在浩荡的春风里和明媚的阳光下展示健康而旺盛的生命,给看倦荒凉一冬的双眼带来视觉上的愉悦;偶尔一片金色的油菜花,为这片绿意浓浓的土地增添一抹亮色。飞虫在麦田里热舞,翅膀在阳光下熠熠放光;而劳动者的身上也渡上了一层金色,浑身充满着力量。他们不是朱自清先生笔下在春天里舒展筋骨的人们,他们在用自身力量争取丰收。在他们的眼里,这土地虽然美丽,但他们需要的是收获。因此,他们唯有在春日的阳光下辛苦耕耘。此时,这里温暖而宁静。热闹是属于那些小虫子们的。它们用飞舞阐释生命,而土地用宁静在孕育生命。
而小麦一旦到了抽穗的时候,天气就立马开始热了起来。
然后是就是“三夏”时刻。“三夏”即夏收、夏种、夏管。一阵干热风,就能让昨天还青青的小麦一夜见黄。当小麦即将成熟的时候,农民们便开始在麦垄里点玉米。玉米不像小麦用播种机来种,也不是像现在用玉米点播机,而是要用一个小铲子铲出一个小坑,在坑里扔上几粒玉米种子。待小麦收割完时,翠绿的玉米苗已经长出寸数来高了。点玉米是很累的一件事,不仅仅是天气已经转热,更重要的是无数次地弯腰直腰,让大多数人感觉腰酸腿疼。点玉米累,而管玉米一点儿也不轻省。等玉米长高一点,就要间苗、锄草。间苗就是让每个坑里出来的三四棵苗留一棵,除了“木秀于林,鹤立鸡群”的玉米苗外,大多数就得拼运气了。尔后便是施肥,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越是下雨的时候,我们越要往地里跑,给玉米施肥。趁着雨水,把营养灌输给正在拔节玉米。拔节的时候如果营养跟不上,就像孩子一样,会耽误其一生的成长,影响收成。再高一点,又要洒药。有的时候用喷雾器打药,有的时候却要用手把药撒在玉米的顶叶的心里,防止一种病虫害,大概是叫钻心虫吧。那种药叫666粉,现在已经禁用了。
当然,给玉米间苗还不是最累的,更累的是给谷子间苗。给玉米间苗拿着铁扒子半弯腰就行,而谷子苗又细又小,得蹲下去,用手一棵棵地揪。每垄不能太稠,也不能太稀。谷子不像小麦。小麦是分蘖的,即一粒小麦长出地面后,会分成若干枝。而谷子却是一棵就是一棵。所以间谷苗很小心,半天也挪不了几步。有怕累的就干脆搬个小马扎坐着给谷子间苗。一天下来,腰也是酸,但却间不出几行来。
然后就等着秋收。
喜欢秋收的味道。这时候已经没有收小麦时的又脏又热又扎,虽然也是累,但少了打仗般的紧张。同时,高高的庄稼被摞倒后,心头一下子便敞亮起来,眼界一下子也宽广起来,再加上庄稼青草特有的味道弥漫在天地间,和夏收的心情就立时大不一样了。地里又满是能跳能飞的促织、蚂蚱、扁担,有时候就会不辞辛劳地能够跑上百十米抓一只拍着翅膀的大蚂蚱。那时候也有蝈蝈,甚至几个小伙伴挖起深沟大壑去找那种短尾巴的老鼠,一般都能在老鼠窝里能掏上半斤粮食。
我想念那时高远的天空;想念那时充实的秋收;想念那一种青草弥漫的味道。
秋收完就是耕地、平地,种小麦。等待冬的光临,然后开始一个新的轮回。
除了一马平川的庄稼地,还有东部的梨区。赵州梨花、雪梨和赵州桥、柏林寺一样,是赵州的名片。梨区也是赵县经济最发达的地方,给赵县税收贡献了不小的力量。那里比较早地就过上了好日子,最早的一批“万元户”基本都是在那边。现在,春天的梨花和秋天的采摘已经成为固有的仪式和活动,既给忙碌的城市居民一片休闲的空间,也多多少少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都让我喜欢和留恋。
最近更是读到了许多关于赵州的文字,里面既有欣喜,也有遗憾。
欣喜文化的厚重,遗憾文化的遗落。
而我的感觉,还不仅仅是文化的遗落,是整个文明的迷失。
尤其是这些年来,更能切身感受到所发生的那些消极变化。
从石家庄往回走,在308国道新宅店向东拐的那条路的南侧,是一条排污沟。在很小的时候,这条排污沟就有。那时候能从水里看到漂浮着各种医用垃圾,味道刺鼻。到后来,周边的人们竟然开始用沟里的水浇灌庄稼地。那时,没人告诉这水能不能浇地,也没人来处理这些散发着恶臭的污水。
而这些年来,这一片突然罹患癌症的人多了起来,不能不让我们怀疑这一片土地是否遭受到了污染,我们所吃的粮食是不是遭受其害。
然而,污染土地的又岂止是这条沟里的水?
曾几何时,人们都开始忙着挣钱。当人们从“斗私批修”的惶恐中走出来,从土地的束缚上摆脱出来,挣钱成了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目标。养家糊口,是每个人的权利;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好,是一个国家的责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方向的指明和黑猫白猫之论的兴起,更是激起了普通百姓的十足干劲。有能力有门路的建个工厂,没能力没门路地到工厂里打个工;有大钱的办个大工厂,有小钱的开个小作坊;胆子大的搞点创新,胆子小的亦步亦趋。马路边上一下子大大小小地建成了各种工厂,那还不够,于是把市内一些大的生产企业也引到家门口。甚至在“招商引资就是生产力”的号召下,从省外甚至从国外引进大的投资项目,所以一切看起来都欣欣向荣,一切看起来都红红火火。等到烟筒冒出黑的或黄的烟来,管道流出黑的或黄的水来,人们脸上都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人们不在乎浓烟滚滚,也不在乎污水四溢,因为这些似乎与大家无关。
而与我们有关的饮用水却越来越深了。
据说,现在村子里浇地的水和饮用的水已经有300米深。这还不是污染最严重的地方。有的地方据说已经打不出好水了。
忽然觉得心里好难受。
记得吗?小时候口渴了,会直接抄起瓢在自家水瓮里舀上半瓢水,咕嘟咕嘟灌下去,连嘴也不用擦一溜烟地跑去玩去了。而如今呢?城市里到处是净水装置,老家的自来水也不敢直接入口,生怕落得个病从口入。
这真是生活的吊诡之处。我们必须承认,农村的生活的的确确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房子建得不比城市差,街道再不是坑坑洼洼的土路,但环境却差强人意。光是堆在村口的垃圾,就成了心腹之患。
几乎每个村的村口,或者旁边的坑沟里,成了垃圾堆积场。塑料产品的使用不仅仅增加了垃圾的堆积速度和数量,更加重了垃圾处理的难度。过去的村里也产生不了多少垃圾,无非只是一些废纸脏土烂日用品,搜集起来一股脑地扔到粪坑里——家家户户都有粪坑,现在被城里人称做连茅圈。一边连着厕所,一边连着猪圈。粪坑出来的是纯粹的有机肥料,等到快耕地的时候,都撒到田间,给庄稼提供健康的营养。现在村里也几乎不再有露天的粪坑了,有机肥料也几乎被化肥替代了,所以垃圾堆放和处理就成了一道大大的难题。好在老百姓并不在意,他们都把垃圾堆到了村口,也似乎与自己毫无关系。
每个村口都是白花花的一片,塑料袋在风中哗哗作响。
这些哗哗作响的白色垃圾,和建设美丽乡村的口号、标语放在一起,多少有些刺眼。
刺眼的还不仅仅是这些,还有一到冬天家家户户冒着黑烟的烟囱。
我们当然不能去矫情地苛责父老乡亲们的烟囱和黑烟。当城市里取暖都上了干净的天然气多年以后,村里的老百姓仍然只能用煤。我们躲在有暖气的屋子里,站在道德的至高点去指责老百姓烧煤本身是不道德的。但有些事让也确实让人感觉些许无奈。
我今年也重新给父母安装了取暖炉,跟父母说一定要烧好煤,别怕花钱。一是烟少一些,二是总得说来也费不到哪里去。父母就跟我讲起村里取暖的一些事情。说本村一位村民,取暖为了省煤,他把从村口垃圾里找的能烧的东西,比如说烂皮鞋什么的,都用来烧火取暖。我说那得多味啊,又有毒。他们说,谁管那个啊。
是啊,谁管那个啊!
村里一些人生活依然很苦,所以他们可以什么都不在乎。但又不都是很苦,却也仍然什么也不在乎。在乎的,只有钱。他们每天心里只是想着怎么样挣更多的钱,今天的晚饭是什么。
他们也可能想着,挣多少钱才能给孩子娶一房媳妇,或者给男方要多少钱,才能把闺女嫁出去。
钱,成了脑子里,口头上须臾不可离开的好东西。
女孩,也成了抢手的商品。
七八十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并没让农村享受到什么红利,相反,出现了严重的后果。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一个村里的光棍数量越来越多。这已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个国家的政策的恶果,只能让一小部分人买单,又是谁之过?
所以,女孩就有资格挑对象,就有资格谈条件。已经流传了好久的“万紫千红一片绿”,“小楼小车小婆婆”,已成为女孩结婚的标配。彩礼钱也是越给越多,让许多家庭不堪重负。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说好的爱情呢?
所以,我曾经对老家淳朴的民风仅存的那些骄傲,正一点点消失怠尽。
“买丝绣作平原君,有酒惟浇赵州土。”李贺的《浩歌》和纳兰性德的《金缕曲》,都使得赵州生动而具体地活在了千古诗词当中。读他们的诗词,我们能够想象出古赵州历史的悲壮与深远,感受到渗透在这方土地上那不绝如缕的文化魅力。
而今,这种文化都被经济的头脑冲得七零八落。
本来,普通老百姓挣钱想过好日子,再正常不过,也无可厚非。但有时候却为金钱扬弃了良知。而那些挣了大钱的暴发户们,又都是一副丑恶的嘴脸。他们用钱来打开挣钱的道路,他们用钱来摆平人和事。淳朴民风,传统礼仪,文化精髓,都已经零落黄泥。
子曰:失礼求诸野。而今,野亦不复存礼。
家里一个亲戚的官司更加印证了这一点。
为钱,一些政府的官员可以与流氓沆瀣一气;为钱,一些法院的法官们可以贪赃枉法。所谓正义,已经沦为被人强奸的少女。当在雾霾里“潘金莲”上访告状时,那些流氓和官员们正享受着阳光海滩、炸鸡啤酒带来的乐趣。
是的,没有这场官司,我曾经对家乡充满了骄傲和亲近,是这场官司,让我充满了愤怒和伤感。
竟不知道一个不大的区域,浑水如此之深,根结如此之复杂。一个个堂皇冠冕的下面,都只是一只只沐猴而已。
不过,我仍然爱我的赵县,也爱我的父老乡亲、朋友同学。
年轻时,我们都努力逃离家乡;现在回头,眼里却满是泪光。
唉!
 招商热线:400-151-2002
招商热线:400-151-2002